2023年12月19日发(作者:那沙)

感觉和知觉的一些问题研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孙沛
一、我们是如何探测外部世界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中,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光、热、压力、振动、分子、辐射、机械力和其他物理能量。但我们的感觉器官能够探测到的物理能量却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察觉到那些超出我们感觉能力的部分。例如,原子辐射、X射线和微波对人是有伤害的,但我们没有对这些能量的感受器。
我们的感觉对信息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拿视觉的感觉选择来说,在包括不同电磁波长的电磁波谱范围内,我们能够看得见的部分为可见光(380~780纳米),此外还存在着我们看不见的部分,如红外线、紫外线、广播发射波、电视发射波以及γ射线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对视觉信息没有选择,来者不拒,那么,我们就像是看同时出现在电视上的一百个频道的画面,什么都不可能看清楚。
有一些感觉系统的感受能力既有上限也有下限。例如,人类最低可以听到20赫兹的声音,最高到2万赫兹的声音。应当说,这样的低阈限低得恰如其分。试想,假如耳朵能听到20赫兹以下的音高,那么,我们将听到自己肌肉运动的声音,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每动一下身体时自己都能听到像摇破木船时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我们该是多么烦恼。
感受器是一种生物性的转换器。转换器是将一种特定能量转换为另一种特定能量的设备。例如,电吉它的原理是将振动转化为电信号,再通过放大和扩音器发出声音,然而,我们却不可能通过光或温度使琴弦发出声音。每一种感觉器官一般对某一种特定范围的能量最为敏感,同时,这种能量也最容易被转换成神经冲动。
在信息转换时,许多感觉在将信息发送到大脑之前会对环境信息进行分析。感觉分析的过程是将其中许多重要特征信息找出来的过程。这些特征就是一个刺激中的基本元素,如线条、形状、边缘、点或颜色等(Ramachandran,1992)。
许多感觉系统的神经环路就是特征探测器,即对特定刺激模式高度敏感的系统。例如,蛙眼特别敏感的是那些小的、移动着的黑点,研究者称这种感觉为“昆虫探测器”(Lettvin,1961)。蛙眼似乎专门用于探测附近的昆虫,换言之,蛙眼只能看移动中的昆虫。因此,如果一个青蛙的身边只有死苍蝇而没有飞着的活苍蝇,它将会饿死。
感觉系统在完成信息的选择和分析之后,还要对信息进行编码。感觉编码过程是将一些显要特征转换成可以被人脑理解的神经信息。
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理心理学家休贝尔(Hubel)和维塞尔(Wiesel)对大脑视皮层单细胞的活动进行直接记录。他们记录不同视网膜区域所对应的每一个细胞的反应。接
下来,他们以不同大小和形状的光照射视网膜并记录相应的大脑细胞激活神经冲动的频率。
结果是令人兴奋的。他们发现许多大脑细胞仅对特定宽度或方位的线条反应。同时这些细胞对一个光点或总体的照明不“兴奋”。还有一些细胞仅对特定角度的线条,或对在一个特殊方向移动的线条反应。这些发现表明大脑中的细胞也是一种特征探测器。似乎大脑首先将进入的信息分为线条、角度、阴影、移动和其他基本特征。接着,其他大脑区域将这些特征结合成一个有意义的视觉经验(Hubel & Wiesel,1979)。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作为特征觉察器的大脑皮层细胞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简单细胞,只能对特定网膜位置上的一定特征进行反应,如果受刺激的网膜位置改变,即使是同样的特征,这种简单细胞也不反应。这类细胞位于大脑皮层表面。另一类细胞叫复杂细胞,它们对一定的特征进行反应,同时又不受网膜刺激部位的影响。这类细胞位于大脑皮层的较深处。还有一类细胞叫做超复杂细胞,它们可以侦察由简单特征组成的复杂特征。
听觉中是否存在声音的特征觉察器?研究发现,听觉神经细胞也是有分工的。听觉中枢神经细胞有40%只反应噪音,而对乐音不反应。这说明神经细胞对噪音和乐音的反应有分工。听觉中枢的另外60%的神经细胞对乐音的反应也有分工:有的只是对音的出现有反应;有的只是在音消失以后才发生反应;有的只是在音出现和消失的一刹那才发生反应;有的在音的频率降低时发生反应;有的在音的频率升高时发生反应。
二、我们如何研究外部物理刺激强度在人的心理上引起的感觉变化
感觉器官使我们能够了解客观现实。但是,我们可以听见的最轻的声音有多轻?可以看见的最弱的光有多弱?心理物理学的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答案。
心理物理学的先驱是费希纳。他是一位哲学家但始终关注心理与物理的关系。他观察到,感觉强度的增加与刺激强度的增长并不是1∶1的关系。刺激的作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并且同已经存在的感觉量相关。经过长期的研究,他于1860年发表了《心理物理学纲要》,为心理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心理物理学方法是在对刺激的物理变化进行测量的同时记录这些变化与心理感觉的联系。心理物理学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导致感觉发生变化的绝对最小物理量是多少?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对一个感觉系统的绝对阈限进行测定。
绝对阈限的测量结果说明一个感觉系统的敏感性。在实际的测量中,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真正的绝对阈限。随着刺激量的增加,对刺激的觉察由不发生到逐渐提高觉察率,直至最终总能觉察出刺激。该过程可以形成一个平滑的S形心理量曲线,这一曲线被称为心理物理函数。该函数表明了心理量(感觉经验)与物理量(刺激的物理强度)之间的关系,它表明感觉从无到有是一个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过程。在实际的测量中,我们一般把有50%的机率能被察觉到的刺激量定义为绝对阈限。
表1 不同感觉通道的绝对感觉阈限
感觉
听觉
味觉
嗅觉
触觉
最小刺激视觉晴朗夜空下48公里处的蜡烛光
安静条件下6米远手表的指针走动的声音
9升水中1茶匙糖的甜味
6间屋子中1滴香水的气味
从1厘米高降落到面颊上的苍蝇翅膀
关于阈限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刺激发生多少的改变,就可以刚好被察觉出来?这就是有关差别阈限的研究。在差别阈限的研究中,产生了心理学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定律,即韦伯定律。韦伯定律的基本含义为:产生一个最小可觉差差别所需的刺激变化量与先前刺激量的比率是一个常数。需要说明的是,韦伯定律仅是一个近似规律,因为它主要适用于中等强度范围的刺激。
表2 不同物理刺激的韦伯系数
刺激类型
闪电
重量
长度
震动(指尖)
响度
气味
亮度
味觉(咸)
韦伯系数
测量感觉阈限的心理物理方法有三种,即最小变化法、恒定刺激法和平均差误法。在以后有关心理物理的研究中,研究者又发展出了信号检测理论,该方法同时考虑了被试的主观判断标准和客观感受阈限两个方面的问题。
三、为什么我们会有颜色视觉
你认为什么颜色最亮,红色、黄色还是蓝色?实际上,视网膜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杆体细胞和锥体细胞,它们在颜色感受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
锥体细胞对光谱黄绿区域是最敏感的。当所有的颜色都在日光条件下测试,那么黄绿光将显得最亮。救火车大量使用黄色和路边工作者穿黄色背心即是这一事实的反应。那么杆体细胞对哪种颜色最敏感呢?实际上杆体细胞并不产生颜色感觉。如果使用非常暗但有颜色的光,眼睛将不会看到任何颜色。尽管如此,对于杆体细胞来说,仍存在着颜色敏感程度上的差别。研究结果表明,杆体细胞对蓝—绿光是最敏感的。于是,在夜晚或暗光条件下,当杆体细胞视觉为主要时,最亮的颜色将是一种蓝或蓝—绿光。由于
这种原因,许多警察和高速公路巡逻车在夜晚工作时均使用蓝色作为紧急灯光。
那么,锥体细胞是如何产生颜色感觉的?颜色视觉的三色理论认为,人眼有三种类型的锥体细胞,每一种各自对红、绿或蓝最敏感。其他颜色是这三种颜色混和的结果,同时由杆体细胞产生黑和白感觉。颜色的颉颃理论认为,视觉将颜色分析为“或者—或者”类型的信息。它假设视觉系统可以对红或绿、黄或蓝、白或黑进行编码,其他颜色是这三对颉颃编码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色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颜色混合现象,但它遇到的挑战是心理原色似乎有四种颜色,即红、绿、蓝和黄。同时,它还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可能有红绿色或黄蓝色。颉颃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色觉异常现象,同时它可以很好地解释颜色后像现象,但它不能很好地解释颜色混合现象。
那么,哪一种颜色理论是正确的?实际上,两者都正确!三色理论适用于视网膜。研究表明,视网膜上存在三种类型的视觉色素,同时每一种色素对不同波长的光最敏感,三种色素的波长峰值基本上落在红、绿或蓝区域(Nathans,et al.,1986)。颉颃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信息在离开眼睛之后视觉通路上所发生的一切,颜色信息的编码似乎是按“或者—或者”颉颃方式进行传递的。所以两种理论都是“对的”。一种解释了在眼睛本身发生了什么,另一种解释了信息在到达人脑的过程中如何被分析,合起来它们解释了颜色视觉。
四、暗适应──让那里亮起来
当适应一个暗房间时,眼睛会发生什么变化?暗适应是在进入黑暗之后,视网膜光感受性发生的戏剧性增加。试想走进一个剧院。如果你从一个亮的大厅进入,那么你需要被领到你的座位。在一段时间之后,你可以看见整个房间的细节。有关暗适应的研究表明,大约需要30~35分钟的完全黑暗才能达到最大的视觉感受性。当暗适应完成时,眼睛可以探测10 000倍弱的光。
什么引发暗适应?像锥体细胞一样,杆体细胞也包括一个光敏感视色素。当被光击中后,视色素漂白或化学分裂(由闪光灯引起的后像就是这种漂白的直接结果)。要恢复光感受性,视色素必须重新混合,但这需要时间。夜视主要是由于视紫红质的增加,即杆体色素的增加。当完全暗适应后,人类眼睛对光的感受性就如同一只猫头鹰的眼睛。
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加速暗适应?杆体细胞对特别的红光不敏感。潜水艇和飞机座舱采用红光照明就是利用了感受性这种缺失特性。战斗机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机务组的预备房间也是同样道理。在每一种情况下,这样做都允许人们快速地进入黑暗而不需要适应。由于红光不刺激杆体细胞,这就好像他们在黑暗中已经呆了很长时间一样。
吃胡萝卜真的能提高视力吗?视紫红质的一种化学“成分”是视黄醛,它是从维他命A合成而来。当缺少维他命A时,仅能制造出少量的视紫红质。这样,一个人由于缺少维他命A可能发展为夜盲。夜盲,即一个人在亮光使用锥体细胞时有正常的视觉,但在夜晚当杆体细胞必须起作用时成为视盲。胡萝卜是维他命A非常好的来源,所以食用
它对一个患有夜视缺陷的人可以提高夜视,但是对任何有正常饮食的人来讲对视觉无任何帮助(Carlson,1994)。
五、一个声音有多大就会造成危害
听力损失的危险依赖于声音的大小和暴露于其中的时间长短。每天处于85分贝以上就可能引起永久性的听力丧失。即使处于120分贝很短的时间(摇滚音乐会)也可能引起暂时的阀限漂移(一种部分的、传递性听力损失)。片刻处于150分贝(喷气式飞机附近)就可以引起永久性耳聋。表3列出了一些日常生活事件的分贝数。
但千万别仅看数据表面。分贝是绘于一个对数轴上的(像地震强度)。每20分贝的增加表示声音总量能够增加10倍。换句话说,一个120分贝的摇滚音乐会不是正常声音60分贝能量的两倍,而是它的1 000倍。
音乐,如噪音一样,也可以引起损害。人们直接坐在高功放音乐会扩音器的前面,也会有相当大的听力损失。由于跳舞或空中练习可以将血液从内耳涌到外耳,也可能导致听力损失。随身听立体声耳机也会带来同样的危险。许多耳机可以达到115分贝或更多。如果你可以听到一个站在你旁边的人耳机里的声音,该音量就可能正在损害他的耳朵。
如果在一个大的声音随后出现耳鸣,毛细胞就可能已经被损害。几乎每一个人偶尔都会有耳鸣,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但是如果重复出现这一警告,你将可能变成永久性的听力困难。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经常性地听大功放音乐会的人,44%的人有耳鸣并且许多人已有部分听力损失(MeyerBisch,1996)。
下一次,你如果处于一个非常大的声音中,请记住分贝表中的数据并且提高注意以防止受到损害(也请记住,为了迅速地保护耳朵,手指永远都在手边)。
表3 一些日常生活事件的分贝表
分贝数
0
30
40
50
60
70
耳朵在未保护的情况下,听力损伤的时间
长时间处于该环境下,听觉开始出现损伤
多于8小时
少于8小时
例子
刚可以被人听到的声音
安静的图书馆,轻声的低语
安静的办公室,远离公路的起居室
有一定距离的交通,冰箱,微风
6米远的空调,会话
繁忙的交通,嘈杂的餐馆
地铁,严重的交通拥挤,0.6米远的闹钟,工厂的噪音
卡车运输,噪音很大的用具,割草机
80
90
100
120
140
180
制衣车间,锅炉房,风钻
摇滚音乐会的扬声器前,雷声
火炮的爆炸,喷气式飞机
航天器的起飞
2个小时
立即损伤
任何暴露都是危险的
不可避免的听觉损伤
六、我们可以闻到多少种不同的气味
嗅觉的适宜刺激是能溶解的、有气味的气体分子。科学家已注意到有特定气味的物质其分子结构在形状上是相当相似的。已标明以下气味的特殊形状:花香、樟脑味、麝香、薄荷味、乙醚。然而这并不意味,如视觉中的三种类型的锥体细胞一样仅存在五种不同的嗅觉感受器。实际上,人类最少存在1 000种以上的嗅觉感受器。
每一种嗅觉感受器仅对一种分子结构的一部分敏感。感受器将分子的不同部分信息传递给大脑。这些信息告诉大脑,“探测到以下这些类型的分子”。大脑接着利用不同的信息模式去辨认标明特定气味的“分子指纹”(Axel,1995)。
现在普遍认为在嗅觉感受器上有不同的“洞”或“口袋”。像拼图游戏一样,当一个分子的一部分与一个相同形状的洞匹配时便产生了化学气味。这被称为锁和钥匙理论。一种气味的产生也与激活的鼻腔部位有关。最后,感受器激活的数目告诉大脑气味的强度(Freeman,1991)。
七、人们似乎有非常不同的口味,为什么会这样
味觉的适宜刺激是能溶于水的化学物质。味蕾是味觉的感受细胞,主要位于舌头上部,在口腔内其他地方也存在一小部分。当食物被咀嚼时,它被粉碎并进入味蕾,那里它激发神经冲动并传送到大脑。味觉感受器的分布是不相同的,你将看到舌头的某些区域对特定的味觉较其他更敏感。其分布是,舌尖对甜味敏感,舌根对苦味敏感,两侧对酸味敏感,而两侧前部对咸味敏感。
除了以上四种味觉品质之外,我们还有更多不同的味道。这是因为我们的味道中还包括了质感、温度、嗅觉,甚至痛(“热”或辣)。除了味觉,嗅对于决定味道也是特别重要的。一小片苹果、土豆和洋葱,当没有鼻子参与时,“品尝”起来几乎完全一样。说味道一半是嗅是毫不夸张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感冒时食物失去它的味道的原因。
像嗅觉一样,甜和苦是当分子与本身具有特定形状的感受器像锁和钥匙匹配时产生的。而咸和酸则是由于带电原子直接进入味细胞末端而激发产生的。许多化学盐尝起来有咸味。酸味可以由酸激发。然而,尝起来甜的化学混合物可以有许多形式。尝起来苦的形式就更多。这里再一次表明,我们对苦化学品的广泛感觉与生存的世界存在如此大量的有苦味的毒素有关(Mclaughlin & Margolskee,1994)。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遗传。大约70%的人对化学苯碳物或PTC尝起来感到苦,而对另外30%的人则没有什么味道。更为普遍地是,味觉敏感性与舌头上味蕾的多少相关。一些人可以少到仅有500个味蕾,而有些人则可以多到10
000个。有许多味蕾的人是“超级味觉家”,他仅需要在咖啡中加入常人一半的糖便感到甜(Pennisi,1992)。
超味觉者倾向于对甜、苦和刺激性物质如酒精和辣椒素有强的味觉。超味觉者女性居多。无味觉者倾向于喜爱甜和油腻的食物,这或许是为什么超味觉者较无超味觉者更苗条的原因(Bartoshuk,Duffy & Miller,1994;Brownlee,1997)。
味觉也随年龄变化。味细胞仅有几天的生命。伴随着年龄的增加,味细胞的替代减慢,因此味觉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儿童时期不喜欢的许多食物现在却有诱人食欲的原因。儿童不吃甘蓝、菠菜、肝脏以及其他,与成人相比,这些东西可能有一种非常不同的味觉体验。除了以上事实,大多数味觉偏好是习得的。
八、我们身体的警卫──痛觉
来自于身体皮肤、肌肉、关节和肌腱的痛,统称为体感痛。我们所感受到的第一种类型的体感痛是由大神经纤维传递的,只有锐利、明显、快速的特点,并且来自特定的区域,它是身体的警告系统。第二种类型的体感痛是由小神经纤维携带的。这种类型的痛是慢的、使人恼烦的、连续固定的、弥漫的和非常不愉快的。它是身体的提醒系统,它提醒大脑身体已被伤害。
身体中的痛感受器远较其他感觉的感受器多,同时其分布也不一样。在膝部之后,每平方厘米平均大约有232个痛点,在臀部每平方厘米有184个,在大拇指每平方厘米60个,在鼻尖每平方厘米44个。痛纤维也存在于内部器官。刺激这些纤维引起脏腑痛。有意思的是,脏腑痛经常会被感到在体表上,距起始点一些距离的某个位置(Chiras,1991)。这种类型的体验称为参照痛。例如,一个有心梗的人可能会觉得左心、臂甚至小拇指痛。
有人(Melzack & Wall,1983)研究了脊柱的痛感觉门控问题。他们注意到,有时人们可以用一种类型的痛消除另一种痛。他们的理论认为,来自不同神经纤维的痛信息都传递到脊柱中相同的神经门控,如果门控由其中一个痛信息“关闭”,那么其他痛信息就不能通过。
那么,如何使门控关闭呢?由大的、快神经纤维携带的信息似乎可以直接地关闭脊髓痛门控。这样便可以阻止慢的“提示系统”痛到达大脑。临床中应用这一效应是通过给皮肤一个轻微的电流刺激。这样的刺激,感觉起来仅像一种轻微的刺痛,但它可以大大地减低许多难以忍受的痛(Long,1991)。来自小的、慢的神经纤维的痛信息似乎有不同的路线。在通过痛门控之后,它们传递到人脑中一个“中央偏离系统”。某些情况下,大脑接着会发送一个信息返回到脊柱,关闭痛门控。
有人(Melzack & Wall)相信有关痛觉的门控理论可以解释针灸的止痛效应。针灸是一种通过在身体插细针以消除疼痛和疾病的中国医学艺术。当针灸师的针被转动、加热或加电,它们便激活了小的痛纤维,接着这些信息通过“中央偏离系统”关闭了剧烈或长期的痛门控(Melzack & Wall,1983)。
针灸还有一个有趣的未能由痛感觉门控理论预言的副效应。接受针灸的人经常报告有飘、轻松或欣快的感觉。如何解释这些感觉呢?答案似乎与能够产生阿片类化学品的躯体能力有关。在与痛进行的战斗中,人脑可以引起脑垂体释放一种称为β的止痛化学品。化学上讲,β内啡呔内啡呔与吗啡因类似。在脑干系统和其他相关于快乐、痛和情绪的人脑区域中发现了大量的内啡呔感受器。针灸和电刺激均可以引起脑内内啡呔的合成。换句话讲,神经系统制造它们自己的“药物”去阻断痛。
九、我们是否可以主动地控制自己的痛
许多例证表明我们可以从心理上控制痛。在印度,僧侣们可以用针刺破他们的面颊或坐在钉床上。在其他的文化中,人们忍受纹身、过度延伸、割、烧及其他,同时似乎只有少量的痛。他们对痛的不敏感是什么原因呢?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缺少正常的痛反应。答案似乎基于以下四种因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它们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下以转变感觉到的痛的程度,它们是焦虑、控制、注意和解释。
焦虑:痛的基本感觉信息可以从对它的情绪反应中分离出来。害怕或高水平的焦虑几乎总是增加痛。
控制:一个持续的反射表明你缺乏对痛的控制。缺乏控制导致增加焦虑和情绪忧伤而增加了痛。如果可以规范、避免或控制一个痛刺激,人们就会少受痛苦。一般地,一个人感觉对一个痛刺激的控制越多,痛也就越少(Kruger & Liebeskind,1984;Wells,1994)。
注意:分散注意同样可以减少痛。痛,尽管它是高度持续的,但也可以像任何其他感觉一样被选择性地“关闭”(最少部分地)。在家中,音乐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散注意任务(Good,1995;Michel & Cheskey,1995)。
解释:对一个痛刺激的理解或解释同样影响痛的程度(Keefe,1982)。例如,如果你重拍一个正在玩耍孩子的后背,你将可能听到大声的笑,但是如果同样的拍击作为一个惩罚就可能带来嚎啕大哭(Bresler & Trubo,1979)。
当我们了解了上述影响因素,我们是否可以应用这些事实来对付疼痛呢?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它们已被应用于生孩子的过程。产前准备训练使用最少量药物或止痛剂来促进生产,就使用了以上所有四种因素。为了对自然分娩做准备,产妇非常详细地学习生产中每一个阶段将发生什么情况。这大大地减轻了她的害怕和焦虑。在生产中,她要注意感觉生产过程中的那些标志并相应地调节自己的呼吸。她的注意力被转移到感觉而不是痛,因此减少了痛(Leventhal,et al.,1989)。另外,通过使用术语“挛缩”而不是“产痛”来维持她积极的态度。最后,由于她数月的准备和她的积极的参与,她感到可以控制任何情况。实验表明,自然分娩技术可以减少平均大约30%的痛。
现在一些牙医有帮助你对痛转移注意力的设备。通过游戏和听耳机里的音乐使病人主动地分心。在其他情况下,集中于一些外部物体也可能帮助你转移对痛的注意力,选择一棵窗外的树、一幅墙上的设计,或一些其他刺激并非常仔细地观察它。沉思中的先
前练习可以对注意力转移产生非常大的帮助,研究表明这种类型的分心对轻度或短暂的痛效果最好。对于长期或强烈的痛,重新解释则更有效(Mecaul & Malott,1984)。
对一个痛的刺激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控制?就是采取对抗刺激。客观地讲,我们的选择是有限的。但你可以让牙医在一个痛的过程开始或结束时给你一个信号,以便你能持续地控制。从前面的痛门控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发送一个轻度的痛信息到脊柱,大脑可以有效地关闭更严重或不可预知的痛神经门控。医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效应。医生已经发现皮肤表面的刺激可以控制身体其他部位的疼痛。例如,一个短暂的、中等痛刺激可以减轻更严重的痛。这样的对抗刺激程序,明显地存在于许多古老的控制痛的技术,这些技术有:使用冰袋,热敷,芥末袋,振动等(Kakigi,et al.,1993;Melzack,1974)。
这些事实表明存在一种减少痛的方法,该方法基于增加控制,对抗刺激和内啡呔的释放。如果你用针刺你自己,你可以轻易地产生和维持相当于许多医疗过程中(接受一个注射、钻牙等)的疼痛。由于你可以控制它,并且它是可以预测的,痛也就不太痛了。
这个事实还可以用来通过在控制刺激之下的第二种痛去掩盖另一种痛。例如,如果你正在补牙,试试用针刺你自己或在指关节上扎针。集中注意力于你创造的痛,并当牙医的工作变得更痛时增加它的强度。
十、我们为什么会晕船、晕车和晕机
上述现象都属于运动病。晕船、晕车和晕机一样,它们的第一个信号是头晕和轻微的空间方位混乱,接下来是脸色苍白、“出冷汗”和恶心等症状。在运动病的大多数类型中,这些信号是呕吐的征兆。
那么,是什么引起运动病呢?运动病直接相关于平衡系统。耳石对运动、加速和重力敏感,而半规管则对平衡敏感。
对运动病最普遍接受的解释是感觉冲突理论。根据该理论,当从平衡系统的感觉不能与从眼睛和身体所接受的信息相匹配时,便会发生头晕和恶心(WarwickEvans &
Beaumont,1995)。通过反复的转圈直到你变得头晕就是一个感觉冲突的例子。这样做让半规管中的液体旋转,当你停下来时,液体仍在搅动,因此大脑认为你的头仍在移动。这引起眼睛不自觉地移动并且使世界看起来仍在旋转。在地面上,来自平衡系统、视觉和动触觉的信息一般是匹配的。然而,在一个起伏的、行进的船、车或飞机上,可能发生严重的不匹配──引起方位混乱和另一种起伏。
为什么感觉冲突会引起恶心?该现象可能与人类的进化有关。在人类生活的早期,许多有毒物质会干扰平衡系统、视觉和躯体的坐标信息。于是,我们逐步进化到我们可以对感觉冲突作出反应,并呕吐排出毒物。
那么,如何减少运动病呢?医学上对空间病的医疗主要使用药物,目前可以通过医生的处方或在药店购买到。值得注意的是,酒精和其他酒类饮料通常会加剧运动病。
苏联宇航员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他们使用一个限制头部运动系统。在船、车或飞机上,尽可能少地移动你的头部也会有一些帮助(Jackson,1994)。你甚至可以用一条毛巾围住脖子以限制头部移动。
为减少感觉冲突,你可以站在船外甲板上。在汽车和飞机上,试着闭上你的眼睛,或作为一个变式,用眼睛盯住一个不移动的点(如地平线)或看地平线上不移动的天空(Stern,et al.,1990)。另外,如果可能,你应躺下。当你水平躺着时,耳石对垂直移动是不太敏感的,并且你的头部移动也少。当然,焦虑可以加重运动病。一些宇航员通过学习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在愉快的、分心的想法或平静的映象来降低运动病。如果你这样做,需要注意慢慢地和深深地呼吸,实际上呼吸就是一个很好的注意对象(Jackson,1994;Nicogossian & Parker,1982)。放松技术可以减少运动病,因为通过放松可以减轻焦虑(Jackson,1994)。
十一、我们的知觉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的知觉是感觉器官先天成熟和后天经验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位医生曾经记录过一位52岁的白内障病人的经历(Gregory,1990),描述如下:S.B.先生从一出生就失明。经历一次手术后,S.B.先生重获光明,他努力学习运用他的视觉。一开始,他只能判断熟悉情境中的距离。一天,医生发现他正要从医院病房的窗户上爬出去,以便更近地看街上行驶的车辆。他的这种好奇心很容易理解,但是必须制止他,因为病房在四楼!
S.B.先生不能从看到的汽车大小判断距离。因为,人只有先熟悉了物体的外形后,才可能利用其大小来判断距离。如果你把自己的左手放在眼睛前方几英寸处,把右手放在一臂长处。右手的视觉像大约只有左手的一半大。但由于你曾无数次从各种不同的距离观察过自己的手,你知道你的左手并没有突然缩小,这就叫做大小恒常性。在知觉中,尽管客体投射在视网膜上的像的大小在改变,但人对这个客体大小的知觉保持不变。我们甚至可以在新生儿身上找到大小恒常性的一些证据(Slater,Mattock & Brown,1990)。
为了准确地知觉手的大小,你必须借助过去经验。一些基本的知觉能力似乎是天生的,比如,看见一张纸上画着的一条线段的能力。但是,许多知觉是建立在先前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例如,一位研究者(Colin Turnbull)曾讲述他把一个非洲俾格米人从茂密的热带雨林带到广阔的非洲大平原的故事。这个俾格米人以前没有在如此远距离地观察物体的经验。因此,当他第一次看见远处的一群水牛时,他认为那是一群昆虫。不难想象,当他乘车靠近这些水牛时是那样的困惑!他得出的结论是:他被巫师愚弄了,因为这些虫子居然在他眼前长成了大水牛(Turnbull,1961)。或许你也有过在不熟悉情境中判断大小的失败体验。当人从高楼或飞机上向下望时,房屋、汽车和人看上去不再正常,而是变得像小玩具。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知觉中的大小恒常性既来自天生,也来自经验。
十二、一个成年人能否适应一个视觉的全新世界
以下有关倒视的实验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倒视实验中,被试被要求戴上一种特殊的眼镜,这样他们看到的世界就是上下颠倒、左右反转的。在戴上这种眼镜后,被试一开始连自己走路、吃饭及做最简单的事都是不可思议的。比如,在去拉门把手时,你会将手伸向相反的方向。
参加实验的被试报告说,头部的运动会使他们感到世界在剧烈晃动,引起了严重的头痛和头晕。然而,几天后,他们居然开始适应这种倒视了。尽管他们看到的世界还不能完全像过去一样,但他们的成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明倒视适应是困难的,但也是可能的。
当这些人达到倒视适应后,他们所看到的事物是否再次正了过来?在戴着倒视眼镜时,人的视觉图像始终保持上下颠倒。但被试们终于学会了进行许多日常的活动,他们眼中的颠倒世界也开始显得相对正常了。在后续的实验中,一些人戴着倒视眼镜能够开汽车;有一个人甚至可以驾驶飞机(Khler,1962)。这就如同让人头朝下倒着坐在那里驾驶!
在一个实验中,被试戴上可以产生严重变形视觉的眼镜,其中那些自己行走的人比在车里被别人推着走来走去的人适应要快(Held,1971)。这一实验说明,通过自主运动与一个新的视觉世界进行互动,对于快速适应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运动会有帮助呢?也许是因为运动可以将肌肉所发出的指令与感觉反馈联系起来。保持固定不动就像是你在看一部古怪电影一样,你不能控制任何活动,因此难以进行知觉学习。
在视觉世界中,再小的扭曲都需要通过知觉学习去适应。例如,物体在水下的外观大小、距离、曲直都发生了扭曲。实验证明,职业潜水员通过适应在水下观察事物,可以正确地知觉那些被扭曲的特征(Vernoy,1989)。
十三、错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们的知觉有时不能正确地表达外部事物的特性,而出现了种种的歪曲现象,这种错误的知觉称为错觉。
心理学能解释所有的错觉吗?错觉有很多类型,主要有几何错觉、形重错觉等。我们还不能解释所有情形下的错觉,一些解释也不能使每个人都满意。一般来说,错觉的产生与我们知觉中的大小恒常性、形状恒常性等知觉特性的综合作用有关。
对于人们熟知的缪勒—莱尔错觉,即你看到的两头为箭头的水平直线显得比两头带“V”字的直线短。量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它们是一样长的。如何解释这种错觉呢?研究者认为,这种错觉可能基于我们对房间、建筑物的边和角的知觉经验(Gregory,1990)。换句话说,三维空间的线索改变了我们对二维图形的知觉(Enns & Coren,1995)。
物体膜像的大小是由物体与人眼之间的距离决定的。如果两个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像大小相同,那么较远的物体被知觉为较大,这一现象称做大小—距离恒常性。有人(Gregory)认为,同样的概念可以用于解释缪勒—莱尔错觉,因为,当你把带“V”头
直线看做比箭头直线离你更远时,你就会把“V”字头的直线看做较长的线。当然,对缪勒—莱尔错觉的这种解释有一个假定的前提条件,即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在多年生活中积累起对直线、锐角、拐角知觉的上述经验。
能否直接证明过去经验可以引起错觉?我们不可能像用小猫一样用人类婴儿做实验,以证明生活环境和文化对上述错觉发展的重要性。幸运的是,我们知道在南非有一个祖鲁人的部族,他们生活于一种“圆”的文化中。祖鲁人的日常生活中极少能碰到直线,他们的棚屋像一个圆的土堆,村落中的棚屋亦排列为一个圆圈,没有直的道路或方形的建筑,他们使用的工具和玩具也都是弯曲的。
那么,当祖鲁人看到缪勒—莱尔错觉图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典型的祖鲁人对于缪勒—莱尔错觉没有任何体验,他们或者认为两条线一样长,或者认为“V”头直线稍稍长一点(Gregory,1990)。这似乎可以证实过去经验和知觉习惯在人类知觉中的重要性。但是,像许多心理学问题一样,我们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有人提出,缪勒—莱尔错觉可能还受到人对直线末端位置知觉的影响(Morgan,Hole & Glennerster,1990)。因此,外观的大小和对直线末端所处位置的不同理解可能是出现错觉的综合原因。
深度知觉线索与日常生活经验有何关联?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图形线索和身体线索来判断深度和距离。这两种类型的线索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知觉效应,叫做月亮错觉,即我们觉得月亮在低空出现时显得较大。
一些人相信那是因为月亮被大气层放大了,其实并没有这么回事。如果你拍摄一组月亮的照片并进行测量,你就会发现,月亮在地平线附近时并不会变大。但是,当月亮在低空时,它看上去确实几乎大了一倍(Plug & Ross,1994)。
当月亮在我们的头顶上时,在它周围没有任何深度线索。而当我们看到月亮在地平线上时,它处在房屋、树木、电线杆和群山的后面,这些物体带入了大量的深度线索,使得地平线看上去好像比头顶上的天空更遥远。月亮错觉的效应很强,如果在照片中出现深度线索,那么,这一效应在照片中也能出现。
由于许多深度线索的存在,地平线看上去比上空更远,这种解释被称为表面距离假说(apparent distance hypothesis)。你可以通过除去深度线索来检验这个假说。当月亮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你可以用纸卷成一个纸筒或是把手握起来当做“望远镜”,去看你刚才见到的大月亮。当你的视野中没有深度线索时,月亮看上去会立刻变小(Plug
& Ross,1994)。
十四、“眼见为实”的说法正确吗
你见过日落吗?你可能说你见到过。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太阳是不会“落”的。相反,是地球本身的转动使我们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使太阳在地平线上逐渐从视野中消失。通过一定练习后,被试可以在“日落”时面对夕阳而立,太阳一动不动,而你感觉到地球的旋转在把你向后带,直到自己看不见远方的太阳(Fuller,1969)。
“太阳落山”可以变成“地球在转”。这两种知觉之间的转换说明,人类观察的结果带有某种局限性,不一定是真实客观的。就像人在经验中获得的大多数概念一样,我们所见到的“日落”是对于一个外部事件的知觉重组。知觉本身包含着感知者的需要、期望、态度、价值观和信念等主观成分。
在法庭上,目击者(eyewitness)的证言对于证明有罪或无罪是很重要的。一目击者说“这是我亲眼所见”时,会对陪审团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目击者的证言经常可能是错的,而陪审团则会被那些自信的证人和“肯定性”的证言所误导。事实上,一个人对其证言的自信程度与其证言的准确性之间几乎毫无相关(Wells,1993)。此外,警察对目击者的询问会使目击者易于相信自己所看见的事,即使看错了他们也不会改口。因此,警察的询问实际上会降低目击者在法庭上所提供的证言的价值(Shaw,1996)。
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正在逐步使律师、法官和警官们相信,目击者的证言难免会有错误。事实上,成百上千的人都是因为目击者的错误而被冤判的(Loftus,1993)。在一个典型的案例中,一位警官作证说,他看见被告在门廊处向受害者开枪;当时他自己与被告和受害者之间的距离约四十米远。心理学家的实际测量结果显示,在这一距离条件下,门廊上昏暗灯光比一只蜡烛发出的光还要弱五分之一,目击者根本不可能看清谁是谁。为了进一步验证,一位陪审团的成员站到这种照明条件下的门廊处,而其他陪审员中没有一个人能辨认出他来。最后,被告被宣判无罪(Buckhout,1974)。
在受到惊吓或威胁以及感到压力的情况下,人所形成的印象特别容易发生扭曲。因此,目击者对犯罪现场的报告常常是不一致的。为了演示这一现象,研究者设计了一场“表演”,让141名被试亲眼看到一位大学教授遭“暴徒”殴打。这一事件发生后,立即对每一个目击者进行了详细的询问,让他们对“暴徒”(实际为一名演员)的相貌、年龄、体重和身高等特征进行描述。之后,又把他们的描述与现场录像进行对照。结果发现,目击者们对“暴徒”特征描述的准确率最多不超过25%(Buckhout,1974)。
受害人能否比目击者记得更多?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目击者与受害者本人对罪犯描述的准确度是相同的(Hosch & Cooper,1982)。因此,如果陪审员更看重受害人的证词,可能会犯严重的错误。值得再次指出的是,对自己的证词很自信的目击者并不比那些显得不太自信的人报告得更准确(Smith,Kassin & Ellsworth,1989)。
在许多犯罪案件中,受害者经常把其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袭击者所用的刀子、枪或其他武器,而没有留意罪犯的相貌、衣着或其他线索(Steblay,1992)。这种“记枪不记人”的知觉倾向往往会给指认犯罪嫌疑人带来一定困难。
总之,日常的知觉、带情绪色彩的知觉和目击者的知觉都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会是完全错误的。要记住,“眼见”但“不实”的情况经常发生。这种认识能帮助你容忍其他人的观点,并更加谨慎地考察自己观点的客观性。
十五、你相信特异功能吗
心灵学,或称心理玄学(parapsychology),是关于超感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简称ESP)和其他特异现象的研究。据称,ESP是一种以特殊方式感知世界的能力,而目前的科学知识还无法解释这种能力。
特异现象(psi phenomena)指一些已知科学规律似乎不能解释的现象,表现为三种基本能力。第一种是神视(clairvoyance),即通过所谓“千里眼”感知事件和获得信息的能力,可以不受距离或物质屏障的影响看到任何东西。第二种是心灵感应(telepathy),即通过“读心术”阅读他人思想的能力,更简单地说,就是看一眼就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三种是预知(precognition),即“先知先觉”或准确预言未来的能力,预知者经常会采用“托梦”的方式来预言未来。心灵学的研究有时还提到第四种能力,那就是心灵致动(psychokinesis),即通过意念驱动无生命物体变化的能力。虽然心灵致动不属于ESP,但也是心灵学家们经常研究的特异现象中的一种。
心理学家对目前所谓的“特异心理能力”的研究持高度怀疑态度。而公众对此却观点不一,各持己见。盖洛普的一项全国性的民意测验发现,美国的成年人中有49%相信ESP的存在(Gallup & Newport,1991)。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科学界对那些心灵学实验提出了哪些质疑。
(1)巧合作用。当一个人有过神视或心灵感应体验之后,就会发现自己难以再对ESP的存在提出质疑。然而,ESP的解释并不能完全令人确信,因为巧合(coincidence)也是一种难以排除的原因。
如果一个预感碰巧被证实是真的,那么,人们往往会将其重新解释为预知或特异现象(Marks & Kammann,1979)。但是,更多的预感最后并没有得到证实,而人们只是将其一忘了之。实际上,尽管人们往往注意不到“巧合”的存在,巧合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也经常期盼某些巧合的事能够发生,因此,出现巧合既不奇怪也不神秘(Alcock,1990)。那些相信ESP的人往往错误地解释巧合中的因果联系,因此很容易在判断日常一些“怪事”时得出错误的结论(Brugger,Landis & Regard,1990)。
(2)心灵学研究结果的可信度问题。早期的心灵学研究中没有一项能够控制并排除作弊或泄露信息的可能性(Alcock,1990)。现代的心灵学家采用的是双盲实验,进行精确的控制,准确记录实验结果,并重复实验。
心灵学研究领域中的欺骗行为甚为猖獗,影响着其研究结果的可信性,例如,一些曾宣布得到正面结果的造假者被揭发出来。有时那些诚实的科学家也会被各种各样的欺骗所愚弄,因此,保持警惕和怀疑的态度是有必要的。如果不能证实被试是否在作弊,那么,越是诚实的研究者就越容易误入歧途(Hyman,1989)。正像一个评论家指出的,那些能证明ESP的测试总是能让人找出“疏漏”(Marks,1990)。总之,特异功能实验的控制越严格,那些“功能”就越不可能出现(Alcock,1990;Hyman,1996)。
(3)概率和偶然性。对特异功能研究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其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功能人”在一次实验中表现出ESP,在后来的实验中又不灵了(Hansel,1980;Hyman,1996)。事实上,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有人能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稳定地保持其特异功
能(Jahn,1982)。ESP研究者认为,这只是一种“衰减效应”,说明特异功能本身是脆质的,不是“想来就来的”(Rhine,1977)。但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当“功能人”的ESP得分在统计上略高于概率时,我们并不能排除偶然运气的原因。然而,如果“功能人”的表演一有问题就说是“这会儿功不在了”,显然是不公平的。
(4)心灵学的研究方法。心灵学家们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他们大部分惊人的研究结果是不能被重复的(Hyman,1996)。即使是在研究人员和实验方法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被试也不能每次表现出相似的结果(Schick& Vaughn,1995)。更重要的是,改进了控制方法的研究更不容易看到ESP(Hyman,1996)。
当然,能够证明ESP不存在的测验结果是不容争辩的。例如,英国的“通灵者”克里斯·罗宾逊宣称自己能预知梦。但是测试结果表明,他的“预知”大大低于概率期望值(Blackmore,1995)。如果这位罗宾逊先生真能预知,知道自己会在测试中出洋相,他还会接受测试吗?
经过近一百三十年的研究,我们目前还不可能确定性地说特异功能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正像我们看到的,对于特异现象实验的严密的观察常常揭露出,一些证明其存在的证据、过程和科学性方面有着严重的问题(Alcock,1990;Hyman,1996;Mark & Kammann,1979;Swets,et al.,1988)。需要提到的是,一项对心灵学家和怀疑论者的调查发现,这两个阵营中的人对特异功能的存在信念都在降低(Blackmore,1989)。然而,作为对特异功能的怀疑者,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只是嗤之以鼻,而是表示我们无法证实其存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一些人通过媒体不加证实、不加批判地大肆宣扬特异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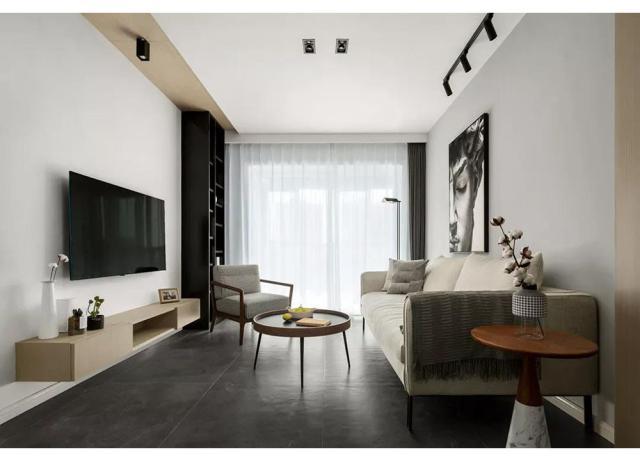
更多推荐
感觉,研究,刺激,可能,知觉,信息,视觉
















发布评论